老费
在我所有的偶像中,老费是唯一在世且还在战斗的人。
很多人听说老费的故事后,都说老费就是白求恩。但老费对此的著名回应是:“我跟白求恩有两点不同。第一,他是外科大夫,我是精神科大夫。外科大夫要尽快解决一位病人的问题,随后去医治下一位病人,而精神科大夫要对一位病人了解很久,才能帮助他消除精神痛苦。第二,毛为白求恩写过一篇文章,但他已不可能为我写一篇文章。 ”
当年我在枫林曾经从图书馆的故纸堆中翻出白求恩的中国战友为他书写的故事,也看过人们为白求恩拍摄的电视剧。白求恩当年作为一个超级不靠谱男青年,曾经辍学一年去当伐木工人。在医学院就读期间,去欧洲抬过担架,年轻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之后长期滞留欧洲大陆四处鬼混。老白一度白天在医院干活,晚上倒卖古董,然后去酒吧舞池寻欢作乐。老白不知如何勾搭上了某富家小家,蜜月旅行就是参观欧洲各大医院,败完了姑娘的嫁妆后,觉得必须要开业赚钱了,于是到底特律行医。老白在底特律目睹了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那时候还没有医保这种东西),也看到同行赚得盆满钵满,于是逐渐就变成了共产党员。老白后来还作为加拿大医生的代表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然后来到了中国,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老费也是加拿大人,不过比老白晚生很多年。老费的青少年阶段是在全世界都洋溢着青春蠢动荷尔蒙的六十年代度过的。老费还记得当年正在上体育课时,老师让大家停了下来,宣布说:孩子们,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总统被刺杀了。(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在当年的加拿大直接说President大家也知道是肯尼迪)老费还记得披头士被介绍到北美后所引发的狂潮,种种记忆的细节栩栩如生,如同发生在昨天。后来,老费上了Mcgill,大学期间正好遇到美国的年轻人到处瞎逛,感觉和我们文革时期的全国青少年大串联差不多。老费于是休学一年,去一栋被游荡的美国青年租下的公寓当经理。休学一年后,他又回到Mcgill,花了一年学完了所有心理学专业的必修课,然后又花了一年上了戏剧专业的课程。本科毕业后,老费开始思考,他是上医学院呢,还是上戏剧学院呢。(不靠谱青年的本质暴露了有木有!)不过老费想了想,还是去医学院吧。于是他去了McMaster University 拿到了MD。值得一提的是,老费表示他在医学院从来没有背过书,也没有考过试。(回想我自己在枫林背的那几十公斤的书,简直难以想象他的医学院有多奇葩!)后来我和一个临床的同学谈到这一件骇人的事情,临床同学表示,加拿大是PBL的发源地,不足为奇。PBL神马的,学医的同学懂的,我就不解释了。
老费在医学院毕业了以后,想要玩一玩。但是还要找实习医生的职位,于是搜索一下,发现新西兰有一个职位可以让他在入职前玩半年,于是他就去新西兰了。在新西兰,他的两个室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室友A是个外科医生,业余爱好是驾船出海,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内心呼唤是——去——中——国!!!那时中国还在文革中,真不知道那个老兄是怎么想的。后来老费在这个哥们儿的影响下,报名参加了一个类似“游学”性质的参观团。可室友A在出发前船坏了,于是放弃了来中国的机会,回去修船去了。但老费心想,俺的钱都交了,不去太不划算了。老费于是还是来中国了,那是1976年,毛大爷还在的时候。
老费和众不靠谱青年到了香港,然后入关。入关后,他们被安排在火车站一个装潢气派的大厅中,坐在沙发上,喝着茶水,听了三四个小时的红歌。这些不靠谱青年都很想笑,但也不敢。听完红歌后,大家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老费在中国一共待了三个星期。老费当时的梦想是远赴亚非拉,拯救第三世界人民于水火之中。老费发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很棒,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工具也很棒,虽然中国的经济条件卫生条件弱爆了,但各种人民健康指标却完爆各种亚非拉国家。老费于是萌生了要在中国学习公共卫生然后去拯救世界人民的想法。
短暂的旅行结束后,老费回到了新西兰。老费的室友B跟老费说,新西兰政府有个项目,可以送新西兰的学生去中国学习两年。老费弱弱地说,可我是加拿大人啊。室友B本来就是新西兰政府的人,爽快地说,那你就说你是新西兰人啊!于是老费冒充是新西兰人民,来到北京学习中文。
老费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毛大爷已经去世了,四人帮也已经倒台了,华国锋也上台了(当老费用英文说出Gang of Four的时候,我总觉得怪怪的。)老费等青年被要求和首都人民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对华主席高呼万岁。那个时候老费想起了少年时,体育老师对孩子们宣布肯尼迪的死讯,他知道他正在见证历史。老费在北京学习了两年中文,之后他想进入中国的公共卫生学院学习,任何一家都可以。但中方表示,他是新西兰来的,是第二世界国家的人民,不能在中国学习公共卫生。于是老费怅怅然地离开了中国。多年后,我在老费的书柜里还翻到了当年的赤脚医生教材,看起来很厉害实用的样子,毕竟当时的口号是中西结合,人畜兼治嘛。
多年以后,老费回忆起了此后的生活:
“觉得我的专业能力当时不够强,于是我去美国华盛顿大学做精神科住院医师。在那里我遇到了Arthur Kleinman(医学人类学的创立人凯博文)教授,他做关于台湾的医疗体系,精神卫生研究。他后来到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医学系的主任, 后来担任人类学系的主任。 他也是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和中国长沙也有合作。于是我选择跟他学习。在华盛顿大学期间,我完成了精神科的住院医师培训,同时在Robert Wood Johnson Fellowship(这个基金会支持了美国国内大量的卫生领域的研究)的支持下,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分别是流行病学和人类学。我毕业后1985年回到大陆,在湖南医科大学做访问学者两年。在此期间给精神科医生做方法学培训。两年结束后我找了全职工作,在80年代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也并不好找,不过我很幸运的在湖北沙市(现荆州)精神病医院找到机会,在那里从1987年工作到1994年,一开始是做精神分裂症家庭医生,同时在很多地方讲研究方法学。在此期间,我也成为国际临床流行病学发展中心的国内代表,在成都的华西医科大和上海第一医科大(现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帮他们建立临床流行病学中心,并带研究生。接下来1994年到2010年我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工作。再后来来到我现在工作的地方–上海交大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回到你的问题说我为什么来到中国,我在1978年完成两年留学生生活时已经定了要在中国做精神卫生方面的研究,当我于1985年完成了精神科医师培训之后我就回到中国并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
老费在UW除了得到了事业上的起步训练外,还得到了一枚贤内助。老费的夫人老毕是一个西雅图的精神科护士。老费在做精神科住院医期间,某日接到医院的电话,让他立刻来医院。老费说今天不该我来的,为什么啊。那护士说,因为你管的一个病人昨天自杀了。就是这个护士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两人一起在中国做了二十多年的自杀研究和干预工作。这样一对夫妇最初竟然也是因为自杀问题而结缘的。老费在西雅图逐渐对自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发现有自杀经历的人比一般的高血压病人要有趣的多。当时有的穷困潦倒的人自杀未遂后被送到医院,老费和他们聊天发现他们其实是想通过自杀的行为来寻求帮助。老费曾经说起一般自杀未遂和自杀的人有显著的不同,也许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吧。
老费1985年来中国时,还把老婆也带过来了。当年老毕一点中文都不会,对中国的印象仅仅限于美国媒体的宣传。也不知道老毕如何下决心放弃了自己在西雅图拥有的一切安逸的生活,跟着老费到了湖北沙市。那时,老毕说,给家人写一封信,要六个月才能到。
老费找到的第一份正是工作是在民政系统的某精神病医院。这不得不说到中国神奇的精神卫生系统。中国的精神病院将近八成是卫生部门主办的,和一般的医院一样。剩下的大部分是民政系统拥有的,用来收留无家可归的患者,以及退伍军人。目前全国还有二十多家公安系统的医院,用于治疗犯罪的患者。精神病专科医院在卫生系统很吃不开,在民政系统里倒是挺有地位的。那家民政系统的医院希望老费这样一个老外能给医院带来名声,就正式聘用了他。
然后,老费就逐渐成为了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老费。老费研究自杀,在《Lancet》上首次发表了关于中国自杀的研究。老费研究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老费汉化了SCID诊断工具,主持了四省的精神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也发表在《Lancet》上,是目前中国精神疾病最高质量的流行病学调查。除此之外的论述著作不可尽数。老费在北京工作了十六年,两个金发女儿说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他在回龙观医院建立了自杀干预中心,开通了自杀干预热线电话。而现在,他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建立了全球精神卫生中心,主持《上海精神医学》的编辑工作,为WHO撰写自杀相关的报告,为CMB订立项目评审标准。老费还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老费还拿到了中国的绿卡。
就这些日子,加拿大首相访华,说要见老费。老费说,那个时候要去西雅图领取杰出校友的奖项,时间挪不开。
老费说,他想要打造一支拥有临床工作者,流行病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的多学科团队,来进一步研究中国的精神卫生和自杀问题。老费还说,他希望CMB能够弄些人来评估监控中国科研监控的质量。如此种种,不可尽数。老毕开玩笑说,你的人生目标还只完成了五分之二。
老费还开玩笑说,美国的医生很多人能够有几套房子,几辆车,还能换几个老婆,自己在中国将近30年,还没有房子,有一部车,一个老婆,车还是老婆在开。当年他们从北京搬家到上海,老婆开着车载着全部的家当还有两只猫咪就来了。老费现在上下班一直坐公交。
老费工作时很严肃,有严重的强迫症,看到参考文献编号的标点没有对齐就觉得闹得慌。老费很执着,对再困难的流行病学现场工作都力求一丝不苟。今年老费去宁夏现场时还亲自带着学生去老乡家做调查,有时老费会被拒访,有时老费却会被老乡们热情招待。大约都是因为他是外国人的缘故。但老费其实也十分幽默风趣,谦和有礼。
写到现在,还没有写老费的名字。老费的中文名是费立鹏,中文名是Michael Phillips。有媒体曾经说,中国是片海洋,费立鹏是个孤岛。老费会抱怨在中国这么多年,今年才第一次拿到中国政府的科研资助。早年还不让外国人购置房产,现如今可以随便买房了,可又买不起了。某日,老毕问我洛杉矶的生活,说小女儿特别想来洛杉矶看篮球比赛,老费撇嘴说,洛杉矶的大学学费那么贵,我们负担不起,还是别想了。
其实,除了白求恩,老费还会让我想起兰安生,John B. Grant。兰安生的父亲是加拿大人,来到中国行医。兰安生出生在中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后来到美国学习了医学和公共卫生后,来到刚建立不久的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当上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卫生系的系主任。他在中国从20年代一直工作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也不知道他后来听说协和医科大学在建国后被改名为了反帝医科大学后会不会有一声叹息。
大话也不说了,这就是我眼中的老费。
其他:
老费的那段访谈回答,点击直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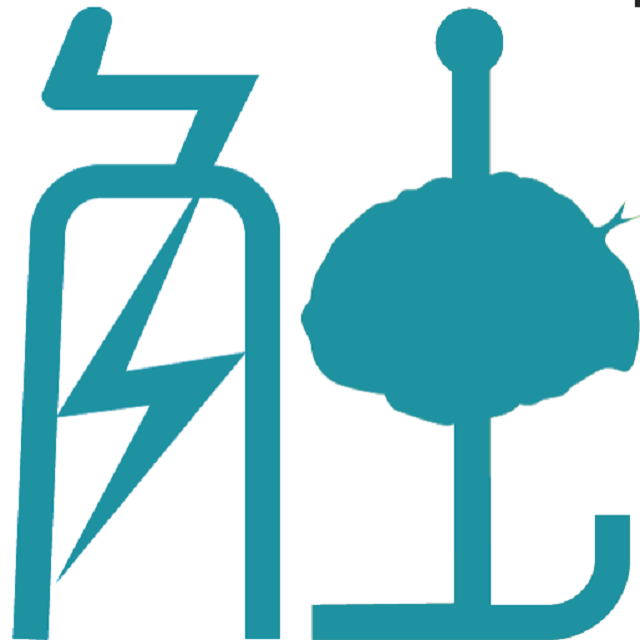




看的我觉得好想去见老费and他老婆老毕~~~~
你如果在上海的话,去找他们呗~
我跑去精卫就能见到嘛见到嘛??等我毕业的,最近小忙。。。
好想冲到二楼见见老费。。。好感动。。。看哭了都。。。
那就去认识下呗~
写的很生动,好文章!
谢谢支持^_^
很偶然的一次机会,见过老费和他的德国太太,老费给人学术研究者感觉,严肃而认真。她太太很爱笑,一口洁白牙齿非常好看,给人阳光慈祥充满爱心的感觉。他们夫妇在回龙观坚持做精神病自杀研究好几年,和张晓丽护士长共同建立了北京精神病救助中心,建立了免费救助电话开展患者家属相互支持帮助活动,为中国精神病自杀救助立下悍马功劳。谢谢老费,谢谢张晓丽,向他们的无私高尚行为致敬。
一个老外让我们中国人都汗颜,爱老费。愿他和他的家人在中国过的开心。
在老费身边工作的人有福了!
在老费身边工作的人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