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回信——关于自杀以及国家干预的粗浅讨论
前段时间,某读社会学Phd的同学写邮件来提到我们的母校最近一直在排查“思想不正常的同学”,因为复旦半年里已经死了三个人了(两个自杀,一个他杀),据说这要影响文明单位指标评比。某同学还问到国家干预精神卫生问题的基础是什么。我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也算是这几年来对这些非主流问题的一些个人想法的总结。

XX:
你的来信里其实包含了很多很大的问题。且容我慢慢道来。但这也只是一个探讨的开始。
先说一些感性的认识吧。自杀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不同人的自杀有不同的原因。比较高质量的中国自杀数据是十几年前的。九十年代末,据估计中国一年自杀死亡的人有28万。(这篇文章发表在2004年的Lancet上,第一作者是费立鹏)但据估计,最近十年以来,中国的自杀率下降了50%。近年来由于没有高质量的大规模调查,所以自杀率的准确数值并不可知。早年,中国人的大部分自杀被认为是“失败的自杀未遂”。相当一部人,尤其是在农村因为家庭问题自杀的人,并不是真的想死,而是想用自杀,或者自杀未遂来达到某种目的,来惩罚身边的家人。这一种情况,我觉得在一位医学人类学家吴飞的《浮生取义》里写得很透彻。但我也看到有人说,要理解九十年代中国农村令人震惊的超高妇女自杀死亡率,必须要理解当年的中国正处在一种从传统大家庭到现代核心家庭的转型期之中。(在有自杀数据的所有地球国家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死亡率超过男性的。)这个观点,我还是姑且赞同的。但现在,中国人自杀的原因可能更接近于其他国家的人们选择自杀的原因,比如绝望,疾病,失败或者其他,而不是为了和家人赌气。以前,农村那种吵了架就喝药的自杀,可以通过管理农药来干预。但现在,干预的难度加大了许多。不得不说,这么多年来,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降低自杀率。
我身边的自杀事件不算少。2011年暑假,我在UCLA交流,在大洋彼岸听说了一个学妹在寝室服毒自杀的事情。那个学妹我还认识,就住在旁边的寝室,非常优秀。没有遗书,也没有解释,甚至买好了三天后回家的车票。2012年暑假,复旦一个老师在家自杀,那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年轻女老师,上课上得很好,人也高挑漂亮。我现在的室友,复旦的,当年他们班里GPA第一的一个同学(貌似是个姑娘)在两人间的寝室自缢死亡。端午节后,我正在和室友感叹复旦大一小孩自杀的事情,一个现在北京某大学心理系读博的同学,找到我说她实验室端午节前一个师姐从实验室九楼跳了下去,博士答辩前一夜,凌晨时分。而这个十月,我又听说了一个十分优秀的一个学弟的死讯。我也曾和临床医学的同学讨论自杀这件事。我赞同朋友的意见,我和她应该不会因为让普通人自杀的事情而自杀,但是如果发生了一些让我们觉得生无可恋的事情,比如感染了疯牛病之类的东西,那么谁也拦不住我们自杀,而且我们一定会成功。所以呢,自杀这种事情,发生了也就是发生了。有的人就是会自杀,拦也拦不住。当然很多人其实根本没有想清楚,也还在贪恋生的温暖,就匆促上路了,那么还是很值得拉一把的。
从自杀说到mental health。mental health的翻译,在国内的精神医学界和心理学界还在争吵。前者觉得是精神卫生,后者觉得是心理卫生。在西方,一般认为90%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但这个比例在中国可能要小很多,但也有研究表明可以高达60%。我个人的意见是,西方的文化中,觉得自杀是不可接受的,但因为精神障碍而自杀,反倒是可以被原谅一些。所以西方学者大约有莫大的动力将精神障碍和自杀联系在一起。但中国文化对于自杀是有一定接受度的,我后来想到端午节不就是用来纪念一个自杀的人么。在西方的语境下,加强精神卫生的服务,可以降低自杀率。但这只是一种猜想,一种假设,没有实际的证据。当然怎么提供服务,提供什么服务也是一个问题。也许并不是没有关联,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合适的精神卫生服务!比如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在幻觉的幻觉和妄想的支配下,或者抑郁患者在自我无法控制的情绪中,发生自杀的行为,这都是精神医学的范畴。某大心理系那个女Phd应该是比较典型的抑郁障碍,凌晨最难过,但满屋子的心理学博士也没有识别出这种危险!当然,自杀不仅仅属于精神医学的范畴。精神卫生的很多问题也不能够仅仅放在生物医学模式下来看。我个人觉得,有精神障碍的人要自杀,这是必须要拉一把的。如果一个人自觉自愿非常理智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地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比如屈原海子之类的。那只是求仁得仁而已。
所以出于爱护学生的角度,关注学生的精神卫生,或者心理健康,都是很有必要的。人群中,1%的人现患严重的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等)。所以有一些学生需要相关的服务,也不奇怪。精神医学和其他西医学科一样,诞生于西方。我个人认为,最初的收容是出于慈善和防止肇祸两种目的。这毋庸置疑是一种针对边缘人的处置。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我始终觉得西方社会,不论欧美,对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期许是在一个很窄的范围的,这可能与我们认为西方社会自由开放的印象相反!但这的确是我的感觉。最新的DSM-V,也就是美国精神科和临床心理的诊断标准,受到许多人的诟病,因为它把很多偏离常规的行为都贴上了疾病的标签!这种出发点,我并不喜欢,很多人也都反对。但不得不说,这个就是事实。如果一个人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不符合社会常规,那么自然会被人认为是“脑子有问题”。我更能接受的,是出于病人痛苦的考虑。这也是事实,却不被很多人认识,包括很多为精神病人呐喊的人。首先,大部分精神疾病给患者带来的是难以描述的痛苦。我同学在实习时遇到过一个小姑娘,上中学,某时突然出现幻听,有人不断跟她说话。她十分恐惧,但又不敢告诉别人。这是一种多么难以言说的痛苦!很多人觉得精神科医生不理解患者的痛苦,我觉得很多时候反倒是家属不一定能够理解患者的痛苦,甚至经常会制造患者的痛苦。我遇到过一个小姑娘,17岁,高二,见到我们就很亲切地问我们叫什么名字,长得也很漂亮。住院前,她长期生活在压抑的家庭环境中,胆小内向,五年不曾说过话!这样的病人,回家后,一旦回到矛盾纠结的环境中,恐怕预后会很不幸。
当然,每个群体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医生的本职自然是处理疾病,关爱病患(虽然往往很不够),但也会有经济和政治上的诉求。政府也有自己的诉求。我国发展精神卫生的历史非常有意思。最初,党和国家大搞生产建设,自然不会关心到这种问题。有一次,某外国首脑访华,车队在长安街上受到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冲撞。于是周恩来牵头开始搞精神卫生的事情。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抗精神病药物也还没怎么发展出来,发展了中国也没有。所以精神病院一开始也就是收容,为了防止出现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国家卫生系统,民政系统和公安系统分别有精神病院,各司其职。但现在也都混收着病人。后来,精神卫生在残联的推动下,在某些地方做了许多福利性的工作,毕竟精神残疾也是残疾的一种。精神卫生,以及残联在90年代的推动者是邓朴方。现在的精神卫生系统还是会依靠残联的力量!然后03年SARS之后,国家发现公卫不牢,地动山摇,于是搞了一篮子公卫项目。精神卫生领域的专家在倒霉了几十年之后,突然发现了改革的春风,立刻便把精神卫生这个东西作为维稳的重要项目递了上去。党和国家立刻就重视起来,钱就来了。浩浩荡荡的“686项目”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在686项目中,对特困病人的筛查和免费治疗也搞起来了,这些项目也算是造福了一大批农村患者。但只能说是给一批过着惨绝人寰的生活的病人(比如被关锁的没法治的贫困病人)提供了最最基本的服务(药物和急性期住院)。总体来说,国家还是以维稳为基调来干这件事情的。这根本不是秘密,这是卫生部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期间的政绩!当然,相关的经济问题,发展问题,和卫生系统别的方面一样,也是复杂的,但是难以进行系统研究的领域,跌足长叹。
这又不得不说到公共卫生这样的问题。现代政府越来越大,什么都要负责。不仅要应急处理,还要做好事前准备,预防为主。当前的公卫系统还是应急导向的。但是还远远不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了。国家现在,一旦发生什么精神病人在帝都上街砍人的事情,就会召集专家问大家怎么办。可这能怎么办呢?就好像你不可能不让人自杀一样。但我认为病人是理应受到基本治疗,并且不应该被疾病,或者治疗以及管理所累的。这就是国家和社会介入的度了。我一直很困惑公共卫生的干预界限在哪里……持续思考中。
祝好!
aran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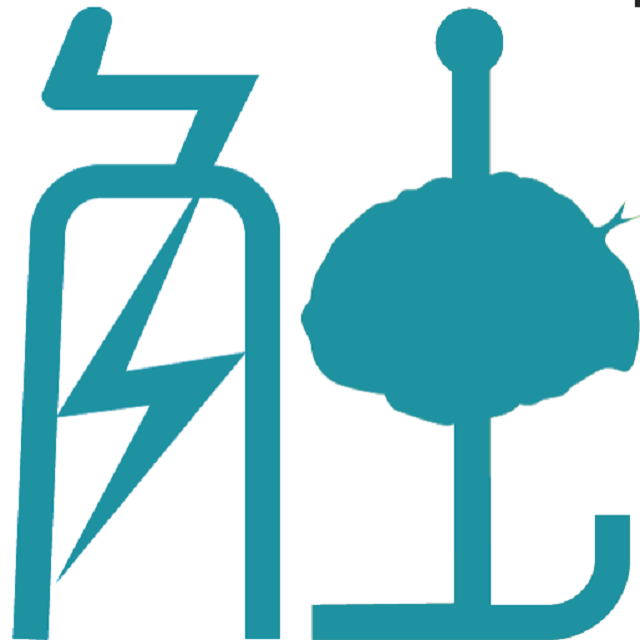


写的太好了
一个朋友层对我说她有一段时间想结束生命,在那一段时间里,她觉得自杀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只是很幸运,那段时间她挺了过来~~~
有坚強意志和崇高理想的人不会自杀,还有看透人生万象而大徹大悟的人不会自杀。第一种人如瞿秋白面对生死从容就义。第二种人淡泊名利,思想境界已经达到可以消解一切人生痛苦和委屈,不会无谓轻生。自杀者大多数是受不了来自內心的痛苦,觉得生不如死;這种痛苦或是自身疾病所致(包括精神方面和肉体方面的),或是外界压力所致(包括政治,经济,生活情感等方方面面)。当事人感到无从投诉,无从发泄,无从解脫,对人生非常绝望的一种冲动造成的。
突然有种想接触精神病人的冲动
有的是机会接触^^ 有些义工活动可以接触到,其实更多的时候精神病人就在我们身边,可能是老师、医生、警察、空姐,总之我见过各行各业的精神病患者,包括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很好的社会功能。
看来我还是应该先了解精神病人的定义
@Shane 嗯嗯,很多人平常认为的精神病患者其实只是一些他们发病时的状态……如果对任何问题感兴趣可以发邮件到jingshenxinli@gmail.com,我们都会回复^_^